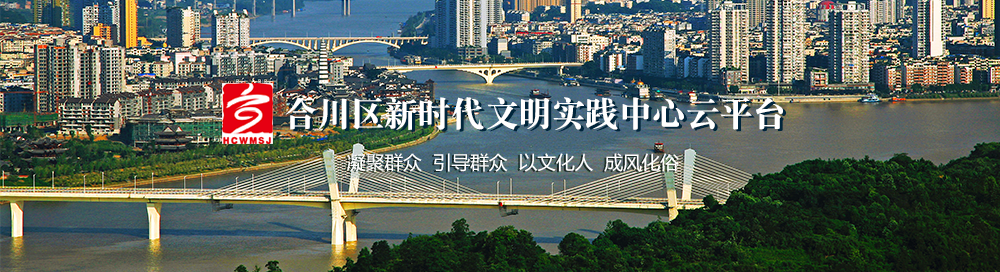
“炮弹像烧红的剃刀擦着头皮飞过,‘滋啦’一声头发就焦了!”8月14日,记者来到重庆市合川区狮滩镇五通村,见到了102岁的抗战老兵乐体全,阳光穿过他银白的发梢,那里曾掠过1944年怒江前线的炮弹破空声——那是死亡最近的一次造访。“再低一寸,怒江就是我的埋骨地。”老人抬手虚抚头顶,指关节嶙峋如老树根。
这位亲历抗战烽火的老兵,记忆里烙着两幅惊心动魄的画面:一幅是头顶呼啸的死神,另一幅是枪口喷发的良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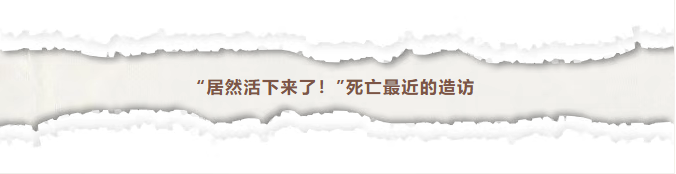
1939年2月,年仅16岁的乐体全毅然加入邻水陆军新编二十九师87团。1943年春末,20岁的他在泸州被编入中国远征军运输十八团辎重部队,成为维系“抗战生命线”的司务长。崇山峻岭间,他带领队伍跋涉,竹篓里背着前线将士的救命粮,骡马驮着沉甸甸的弹药箱。

“怒江的水是红的,漂着弟兄们的帽子……”老人回忆起1944年反攻战役时声音发颤,浑浊的眼泪在深陷的眼眶里打转,他所在的运输团奉命支援强渡怒江,临时搭建的浮桥在日军的炮火中如风中残叶。“子弹‘嗖嗖’钻进脚边的泥,噗噗作响,溅起的泥点都是热的!驮着弹药的骡子被爆炸声惊得发了狂,嘶鸣着就往江心跳,连人带牲口眨眼就被卷进红得发黑的急流里,连个泡都冒不出来……”
就在他奋力拉扯另一匹受惊骡子的缰绳时,一声尖厉到足以刺穿耳膜的呼啸破空而至!乐体全几乎是凭着战场上磨砺出的本能,猛地向前扑倒。“轰!”一发炮弹掠过他的头皮,震耳欲聋的爆炸在身后咫尺之地响起,狂暴的气浪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将他狠狠按在地上,碎石、泥土、滚烫的弹片雨点般砸落。灼热的气流瞬间燎焦了他鬓角的头发,皮肤传来一阵火辣辣的刺痛。
当令人窒息的硝烟稍稍散去,他挣扎着抬起头,眼前的景象让他血液几乎凝固:刚才站立处附近,一棵碗口粗的树被齐刷刷削断,燃烧的残枝就倒在他脚边不足一米的地方!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硫磺味、血腥味和皮肉焦糊的可怕气味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,确认还在脖子上,又动了动脚,还能动弹……那一刻,巨大的后怕像冰冷的江水瞬间淹没了他,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。劫后余生的庆幸与目睹战友殒命的悲怆交织在一起,几乎让他窒息。“我居然活下来了……”这念头像闪电划过他空白的脑海,带着难以置信的震颤和一种近乎虚脱的无力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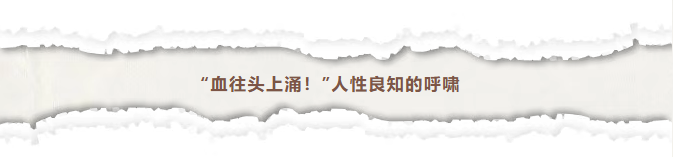
战场的残酷中,人性的光芒往往在刹那间迸发。一次运送军粮返程途中,行至僻静山坳,密林深处骤然传来女子撕心裂肺的哭喊。乐体全心中一紧,循声拨开浓密的树叶,他看见几名日军正撕扯一名农妇的衣裳,女子挣扎哭嚎,衣襟已被扯破。
“血往头上涌!”老人浑浊的眼中倏地闪过厉色,“顾不得多想,我端起‘汉阳造’(注:当时中国军队常用步枪),对准最近那个日军的后背就是一枪!”枪声在山谷炸响,中弹的日军扑倒在地。另外的人惊愕回头,乐体全甚至能看到对方眼中凶光毕露的杀意。“他们‘哇呀’怪叫着拔枪朝我冲来!”老人急促地喘息,仿佛重回那生死一瞬,“我扭头就往密林深处钻,子弹‘噗噗’打在身后的树干上,树皮乱飞……” 乐体全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,在藤蔓荆棘中拼命奔逃,身后的呼喝与枪声渐渐稀落。
“那是我这辈子开得最‘莽撞’的一枪。”乐体全的声音低了下去,“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,不能看着同胞遭难!可开了枪……也就捅了‘马蜂窝’。”老人喉头滚动了一下,浑浊的眼底泛起复杂的波澜。“三四个日军,追着我……跑的时候,腿肚子都在转筋,林子里树枝刮得脸生疼,子弹就在耳朵边上‘嗖嗖’地飞!可要是再选一次……”他猛地抬起头,佝偻的脊背竟挺直了一瞬,眼中迸射出如当年扣动扳机时那般决绝的光,“那枪,我还是得开!就算只吓跑日军,也算值了!”
1949年,历经十年戎马的乐体全解甲归田。硝烟散尽后,这位曾穿梭于枪林弹雨的司务长,重新拾起锄头,在故乡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七十余载。
采访临近尾声,老人颤巍巍地拿出几枚珍藏许久的纪念章,勋章表面流转着温润而坚韧的光芒。“这是国家给我的……”老人轻声说道,那一刻,勋章的光芒仿佛穿透了时光,照亮了老人平静的眼眸深处——那里沉淀着怒江的硝烟、密集的枪声、同胞的哭喊,以及一个民族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“那怒江的水声,还有那个女人的哭喊……有时半夜还会在耳朵边响。”老人摩挲着纪念章冰凉的边缘,低语道。院角倚着他当年用过的旧锄头,木柄早已磨出深凹。而七十多年前那杆在危急时刻喷出火舌、救人也自救的“汉阳造”,则永远留在了异乡的密林深处,连同那个农妇的遭遇,一同沉入了历史的硝烟。